|
|
1978еєіеƐ姩пЉМеЃЙеЊљеЗ§йШ≥е∞Пе≤ЧжЭС18дљНеЖЬж∞СеЖТзЭАй£ОйЩ©пЉМеЬ®еЬЯеЬ∞жЙњеМЕиі£дїїдє¶дЄКжМЙдЄЛдЇЖзЇҐжЙЛеН∞пЉМжЛЙеЉАдЇЖдЄ≠еЫљжФєйЭ©зЪДеЇПеєХгАВеЬ®28еєіжФєйЭ©зЪДеОЖеП≤дЄ≠пЉМдЇІзФЯињЗињЩж†ЈйВ£ж†ЈзЪДдЇЙиЃЃпЉМжФєйЭ©зЪДжЧ©жЬЯпЉМдЇЙиЃЇињЗеЃЙеЊљвАЬеВїе≠РзУЬе≠РвАЭзЪДйЧЃйҐШпЉЫеЉАеКЮзїПжµОзЙєеМЇжЧґпЉМдЇЙиЃЇињЗвАЬеІУз§ЊињШжШѓеІУиµДвАЭзЪДйЧЃйҐШпЉЫеЬ®2006еєівАЬеНБдЄАдЇФвАЭиІДеИТеЉАе±АдєЛжЧґпЉМдЄАдЇЫжЬЙиѓЖдєЛе£ЂжМЗеЗЇпЉЪжФєйЭ©е¶ВжЮЬжМЙзЕІз§ЊдЉЪдЄїдєЙеЄВеЬЇзїПжµОдљУеИґзЪДи¶Бж±ВжЭ•и°°йЗПпЉМдЄНдїЕе∞ЪжЬ™еЃМжИРпЉМиАМдЄФињШйЭҐдЄізЭАдЄНе∞СдЇЯеЊЕиІ£еЖ≥зЪДзЯЫзЫЊеТМе§НжЭВйЧЃйҐШпЉМжФєйЭ©зЪДеЇФиѓ•ињЫеЕ•жЫіжЈ±гАБжЫіеЃљзЪДе±ВйЭҐгАВдЄАдЇЫдЇЇиЈ≥еЗЇжЭ•пЉМеИ©зФ®ељУеЙНжФєйЭ©дЄ≠еЗЇзО∞зЪДдЄАдЇЫзЯЫзЫЊпЉМе¶ДеЫЊзїЩжФєйЭ©жЦљеК†еОЛеКЫпЉМйГ®еИЖдЇЇзФЪиЗ≥иѓђиФСжЈ±еМЦжФєйЭ©жШѓвАЬ饆и¶ЖDANGеТМZHENG FUвАЭпЉМжККеОЖеП≤йЗНжЦ∞еЄ¶еЫЮйВ£дЄ™вАЬиґКз©ЈиґКеЕЙиН£вАЭзЪДжЧґжЬЯгАВињЩдЇЫдЇЇж≠¶жЦ≠зЪДиЃ§дЄЇеТМеє≥жЉФеПШзЪДдЄїи¶БеН±йЩ©жЭ•иЗ™зїПжµОйҐЖеЯЯпЉМињЩе∞±жШѓвАЬеЈ¶вАЭпЉМеПѓдї•зІ∞дєЛдЄЇвАЬжЦ∞еЈ¶жіЊвАЭгАВ
дїКеєі6жЬИ5жЧ•пЉМгАКдЇЇж∞СжЧ•жК•гАЛеПСи°®дЇЖзљ≤еРНжЦЗзЂ†гАКжѓЂдЄНеК®жСЗеЬ∞еЭЪжМБжФєйЭ©жЦєеРСдЄЇеЃЮзО∞вАЬеНБдЄАдЇФвАЭиІДеИТзЫЃж†ЗжПРдЊЫеЉЇе§ІеК®еКЫеТМдљУеИґдњЭйЪЬгАЛпЉМжЦЗзЂ†дЄАеЉАеІЛе∞±жМЗеЗЇпЉМдїКеєівАЬдЄ§дЉЪвАЭжЬЯйЧіпЉМиГ°йФ¶жґЫжАїдє¶иЃ∞еЬ®дЄКжµЈдї£и°®еЫҐеЃ°иЃЃжЧґеПСи°®иЃ≤иѓЭзЪДи¶БзВєе∞±жШѓпЉЪеЉЇи∞Ги¶БеЬ®жЦ∞зЪДеОЖеП≤иµЈзВєдЄКзїІзї≠жО®ињЫз§ЊдЉЪдЄїдєЙзО∞дї£еМЦеїЇиЃЊпЉМиѓіеИ∞еЇХи¶БйЭ†жЈ±еМЦжФєйЭ©гАБжЙ©е§ІеЉАжФЊгАВ
жЦЗзЂ†жМЗеЗЇпЉЪеїЇзЂЛеТМеЃМеЦДз§ЊдЉЪдЄїдєЙеЄВеЬЇзїПжµОдљУеИґпЉМжШѓдЄАеЬЇжЈ±еИїзЪДз§ЊдЉЪеПШйЭ©пЉМдєЯжШѓйЭЮеЄЄе§НжЭВзЪДз§ЊдЉЪз≥їзїЯеЈ•з®ЛгАВжИСеЫљи¶БеїЇжИРеЃМеЦДзЪДз§ЊдЉЪдЄїдєЙеЄВеЬЇзїПжµОдљУеИґпЉМињШжЬЙеЊИйХњзЪДиЈѓи¶Биµ∞пЉМиЃЄе§ЪиІДеЊЛжАІзЪДдЄЬи•њжИСдїђињШдЄНзЖЯжВЙгАВзО∞еЬ®пЉМ嶮зҐНзїПжµОз§ЊдЉЪеПСе±ХзЪДдЄАдЇЫдљУеИґжАІгАБжЬЇеИґжАІйЪЬзҐНеТМеЉКзЂѓињШж≤°жЬЙеЃМеЕ®жґИйЩ§пЉМеРМжЧґеПИеЗЇзО∞дЇЖдЄНе∞СжЦ∞жГЕеЖµжЦ∞йЧЃйҐШжЦ∞зЯЫзЫЊгАВжФєйЭ©еЉАжФЊдї•жЭ•зЪДеЃЮиЈµзїПй™МеСКиѓЙжИСдїђпЉМеК†ењЂзїПжµОз§ЊдЉЪеПСе±ХгАБиІ£еЖ≥еЙНињЫдЄ≠зЪДзЯЫзЫЊеТМйЧЃйҐШпЉМж†єжЬђеЗЇиЈѓеЬ®дЇОжЈ±еМЦжФєйЭ©гАВеП™жЬЙжЈ±еМЦжФєйЭ©пЉМжЙНиГљињЫдЄАж≠•иІ£жФЊеТМеПСе±Хз§ЊдЉЪзФЯдЇІеКЫпЉМдљњдЄКе±ВеїЇз≠СињЫдЄАж≠•йАВеЇФзїПжµОеЯЇз°АеПСе±ХзЪДи¶Бж±ВпЉМдљњдЄ≠еЫљзЙєиЙ≤з§ЊдЉЪдЄїдєЙеІЛзїИеЕЕжї°зФЯжЬЇеТМжіїеКЫпЉЫжЙНиГљдљњеЕ≥з≥їзїПжµОз§ЊдЉЪеПСе±ХеЕ®е±АзЪДйЗНе§ІдљУеИґжФєйЭ©еПЦеЊЧз™Бз†іжАІињЫе±ХпЉМињЫдЄАж≠•еЃМеЦДиРљеЃЮзІСе≠¶еПСе±ХиІВзЪДдљУеИґжЬЇеИґдњЭйЪЬпЉМжО®еК®зїПжµОз§ЊдЉЪеПИењЂеПИе•љеПСе±ХпЉЫжЙНиГљжЫіе•љеЬ∞иІ£еЖ≥дЇЇж∞СзЊ§дЉЧжЬАеЕ≥ењГгАБжЬАзЫіжО•гАБжЬАзО∞еЃЮзЪДеИ©зЫКйЧЃйҐШпЉМзЬЯж≠£еБЪеИ∞еПСе±ХжИРжЮЬзФ±дЇЇж∞СеЕ±дЇЂгАВ
ињЩзѓЗз§ЊиЃЇеЕ®жЦЗзЪДиРљиДЪзВєпЉМе∞±жШѓи¶БеЕЛжЬНдЄАеИЗйШїеКЫпЉМжККжФєйЭ©еЬ®жЫіжЈ±гАБжЫіеЃљзЪДе±ВйЭҐзїІзї≠жЈ±еМЦдЄЛеОїгАВињЩдЄ™еЯЇи∞ГпЉМзїЩдЇЖвАЬжЦ∞еЈ¶жіЊвАЭдЄАиЃ∞еУНдЇЃзЪДиА≥еЕЙгАВжИСдЄ™дЇЇиЃ§дЄЇињЩиЃ∞иА≥еЕЙзЕљеЊЧеПКжЧґпЉМзЕљеЊЧењЕи¶БгАВйВ£дЇЫвАЬжЦ∞еЈ¶жіЊвАЭгАБвАЬе¶Цй≠ФжХЩеЊТвАЭгАБвАЬеУДеЃҐвАЭеЇФиѓ•зЙҐиЃ∞ињЩиЃ∞иА≥еЕЙгАВ
вАЬеЈ¶вАЭжШѓдЄАзІНдє†жГѓеКњеКЫпЉМ1957еєіеЉАеІЛпЉМжИСеЫље∞±еЬ®зКѓвАЬеЈ¶вАЭзЪДйФЩиѓѓпЉМ1958еєіжРЮвАЬе§ІиЈГињЫвАЭпЉМзїУжЮЬдљњдЇЇж∞СзФЯжіїжЫіеЫ∞йЪЊпЉМ1959пЉН1961еєідЄЙеєіиЗ™зДґзБЊеЃ≥жЬЯйЧіпЉМињЮеРГй•±й•≠зЪДйЧЃйҐШйГљжЧ†ж≥ХиІ£еЖ≥пЉМжЫідЄНи¶БиѓіеИЂзЪДгАВиЩљзДґ1962еєідї•еРОзїПжµОйАРж≠•жБҐе§НпЉМдљЖжШѓеП¶дЄАеЬЇжЫіе§ІзЪДзБЊйЪЊпЉНпЉНпЉНвАЬжЦЗеМЦе§ІйЭ©еСљвАЭеЉАеІЛдЇЖпЉМдЄАжРЮе∞±жШѓеНБеєігАВињЩеНБеєіпЉМеЊИе§ЪиАБеє≤йГ®гАБдЄУеЃґгАБе≠¶иАЕйБ≠еИ∞ињЂеЃ≥пЉМеЫљеЃґдЄїеЄ≠еИШе∞Се•З襀жЙУдЄЇвАЬиµ∞иµДжіЊвАЭгАБвАЬе§Іж±Йе•ЄвАЭгАВињЩеНБеєіпЉМеЗЇдЇЖеЊИе§ЪжА™дЄЬи•њпЉЪи¶БдЇЇдїђеЃЙдЇОиіЂеЫ∞иРљеРОпЉМиѓідїАдєИвАЬеЃБи¶БиіЂеЫ∞зЪДз§ЊдЉЪдЄїдєЙпЉМдЄНи¶БеѓМи£ХзЪДиµДжЬђдЄїдєЙвАЭгАВдљЖдЇЛеЃЮдЄКпЉМйВ£йЗМжЬЙдїАдєИиіЂеЫ∞зЪДз§ЊдЉЪдЄїдєЙгАВжЦЗйЭ©зїУжЭЯпЉМдљЖдЄ≠еЫљињШеЬ®вАЬеЈ¶вАЭзКґжАБдЄЛеЊШеЊКдЇЖдЄАдЄ§еєіпЉМељ±еУНжЦ∞дЄ≠еЫљиЊЊеИ∞дЄЙеНБе§ЪеєіпЉМеПѓи∞Уж†єжЈ±иТВеЫЇгАВ
иЩљзДґ1978еєіе∞Пе≤ЧжЭСзЪДеЖЬж∞СжЛЙеЉАдЇЖжФєйЭ©зЪДеЇПеєХпЉМдљЖжХідЄ™дЄ≠еЫљз§ЊдЉЪзЪДзїПжµОжФєйЭ©жШѓеЬ®1980еєіжЙНзЬЯж≠£еЕ®йЭҐеЉАе±ХгАВдїО1981еєіпЉН1983еєіињЩжЃµжЧґпЉМжФєйЭ©дЄїи¶БеЬ®еЖЬжЭСињЫи°МпЉМ1984еєіиµЈиљђеЕ•еЯОеЄВжФєйЭ©гАВзїПжµОеПСе±ХжѓФиЊГењЂжШѓеЬ®1984еєіпЉН1988еєіињЩжЃµжЧґжЬЯгАВињЩжЃµжЧґжЬЯеИЫйА†еЈ•дЄЪжАїдЇІеАЉ6дЄЗдЇње§ЪеЕГпЉМеє≥еЭЗжѓПеєіеЬ®21.7пЉЕгАВеЃЮдЇЛж±ВжШѓзЪДиѓіпЉМињЩжЃµжЧґжЬЯпЉМжИСеЫљзЪДеЫљж∞СзїПжµОжШѓдЄКдЇЖдЄАдЄ™жЦ∞зЪДеП∞йШґгАВ
ињЩжЃµжЧґжЬЯдЇІзФЯзЪДйЧЃйҐШпЉМдЄАжЦєйЭҐжШѓеЬ®жДПиѓЖ嚥жАБдЄКпЉМеП¶дЄАжЦєйЭҐжШѓеЬ®зїПжµОињРи°МдЄКгАВжДПиѓЖ嚥жАБдЄКзЪДйЧЃйҐШпЉМеЕЈжЬЙдї£и°®жАІзЪДжШѓ1984еєіеЃЙеЊљвАЬеВїе≠РзУЬе≠РвАЭгАВдїЦйЫЗеЈ•еИґдљЬеТМйФАеФЃзУЬе≠РпЉМзІ∞дЄЇвАЬеВїе≠РзУЬе≠РвАЭпЉМеЊЧдї•иЗіеѓМгАВйЧЃйҐШе∞±еЗЇжЭ•дЇЖпЉМеЊИе§ЪдЇЇиѓідїЦиµЪдЇЖдЄАзЩЊдЄЗпЉМеПИжШѓвАЬйЫЗеЈ•вАЭеИґдљЬеТМйФАеФЃпЉМзЃЧдЄНзЃЧвАЬиµДжЬђдЄїдєЙзЪДиЛЧвАЭпЉМдЄїеЉ†и¶БвАЬеК®вАЭдїЦгАВињШжЬЙдЄАдЄ™еЕЈжЬЙдї£и°®жАІзЪДпЉМе∞±жШѓеЬ®еКЮзїПжµОзЙєеМЇжЧґпЉМзЙєеМЇвАЬеІУз§ЊињШжШѓеІУиµДвАЭзЪДйЧЃйҐШгАВдљЖжШѓжЈ±еЬ≥зЪДеїЇиЃЊжИРе∞±пЉМжШОз°ЃзЪДеЫЮз≠ФдЇЖињЩдЄ™йЧЃйҐШгАВзїПжµОињРи°МдЄКпЉМдЄїи¶БйЧЃйҐШзЙ©дїЈж≥ҐеК®жѓФиЊГе§ІгАБйЗНе§НеїЇиЃЊжѓФиЊГдЄ•йЗНпЉМеЫ†ж≠§зїПжµОжФєйЭ©еЬ®1989еєіиµЈињЫеЕ•ж≤їзРЖжХій°њйШґжЃµпЉМдЄАзЫіеїґзї≠еИ∞1992еєіпЉМињЮзї≠ињЫи°МдЇЖдЄЙеєізЪДж≤їзРЖгАВ
дїО1992еєіиµЈпЉМжФєйЭ©ињЫеЕ•дЄАдЄ™жФїеЭЪйШґжЃµпЉМдєЯжШѓдЄАдЄ™зЧЫиЛ¶зЪДињЗз®ЛгАВињЩдЄ™йШґжЃµеПЦеЊЧзЪДжИРе∞±е§ІеЃґйГљжЬЙзЫЃеЕ±зЭєпЉМзФЯжіїжЭ°дїґзЪДжФєеЦДпЉМеЫљйЩЕеЬ∞дљНзЪДжПРйЂШйГљжШѓиГЬдЇОйЫДиЊ©зЪДдЇЛеЃЮпЉМжЧ†йЬАйЗНе§Не§ЪиѓігАВдїОеЃПиІВдЄКжЭ•зЬЛпЉМињЩдЄ™йШґжЃµзїПжµОдЄКзЪДдЄїи¶БйЧЃйҐШжШѓпЉЪ
1гАБеРДи°МдЄЪгАБеРДдЄ™зїПжµОйҐЖеЯЯдєЛйЧіжФєйЭ©зЪДињЫе±ХдЄНеЭЗи°°пЉМи°МдЄЪеЈЃиЈЭе§ІпЉМеЯОдє°еЈЃиЈЭе§ІгАВзФµеКЫгАБйАЪиЃѓгАБз®АжЬЙиµДжЇРз≠ЙеЮДжЦ≠и°МдЄЪдЄОзЇЇзїЗгАБеЖґйЗСгАБеИґйА†з≠Йи°МдЄЪеЈЃиЈЭйАРеєіжЙ©е§ІпЉЫ
2гАБжФєйЭ©зЪДжО®ињЫдЄОжАЭжГ≥иІВењµиљђеПШдєЛйЧідЄНеє≥и°°гАВз™БеЗЇи°®зО∞еЬ®еѓєеЫљжЬЙдЉБдЄЪзЪДжФєйЭ©жЦєйЭҐгАВзО∞йШґжЃµзЪДеЫљдЉБжФєйЭ©пЉМеП™жШѓзЃАеНХзЪДеБЬзХЩеЬ®и∞ГжХійЪґе±ЮеЕ≥з≥їгАБжФЊжЭГиЃ©еИ©дЄКпЉМеєґж≤°жЬЙзЬЯж≠£еЃЮзО∞йАЪињЗдЇІжЭГеИґеЇ¶зЪДжФєйЭ©жЭ•иІ£еЖ≥еЫљжЬЙдЉБдЄЪзЪДзІѓеЉКпЉМеП™жГ≥иљђжНҐжЬЇеИґиАМдЄНжЙУзЃЧжФєеПШеИґеЇ¶пЉЫ
3гАБзїПжµОдљУеИґжФєйЭ©дЄОи°МжФњдљУеИґжФєйЭ©ж≠•и∞ГдЄНдЄАиЗіпЉМеРОиАЕдЄ•йЗНжїЮеРОдЇОеЙНиАЕгАВи¶БеїЇзЂЛз§ЊдЉЪдЄїдєЙеЄВеЬЇзїПжµОпЉМеОЯжЬЙи°МжФњдљУеИґдєЯеЇФељУзЫЄеЇФињЫи°МжФєйЭ©пЉМдЄЇзїПжµОдљУеИґжФєйЭ©еИЫйА†жЭ°дїґпЉЫ
4гАБж≥ХеЊЛеИґеЇ¶еїЇиЃЊиРљеРОгАВеЫљеЃґеЬ®еЃПиІВдЄКеѓєеЄВеЬЇзЪДи∞ГжОІпЉМдЄїи¶БеП™иГљйЗЗзФ®йЧіжО•зЪДжЙЛжЃµеТМеКЮж≥ХгАВдљЖеЬ®ж≥ХеИґеїЇиЃЊињЩдЄ™йГ®еИЖпЉМжИСдїђињШжѓФиЊГиРљеРОгАВй¶ЦеЕИпЉМзЂЛж≥ХзЪДиМГеЫіеЊИдЄНеЕ®пЉМиЗ≥дїКж≤°жЬЙдЄАйГ®еЃМжХізЪДдЉБдЄЪеЄВеЬЇи°МдЄЇзЪДж≥ХеЊЛгАВеЕґжђ°пЉМиЃЄе§ЪзЂЛж≥ХдЄНжШѓзФ±зЂЛж≥ХжЬЇеЕ≥дЄУйЧ®зїДзїЗиµЈиНЙпЉМиАМжШѓзФ±еРДдЄїзЃ°зЪДйГ®йЧ®иіЯиі£пЉМйГ®йЧ®жЭГеКЫеИ©зЫКзЪДзЧХињєеЊАеЊАеНБеИЖжШОжШЊгАВвАЬжФњз≠ЦвАЭеТМвАЬж≥ХеЊЛвАЭзЪДзХМйЩРж®°з≥КдЄНжЄЕгАВ
ињЩжЃµжЧґжЬЯжЪійЬ≤еЗЇзЪДз§ЊдЉЪйЧЃйҐШжШѓпЉЪиіЂеѓМеЈЃиЈЭињЗе§ІпЉМз§ЊдЉЪжФґеЕ•еИЖйЕНдЄНеРИзРЖгАВиіЂеѓМеЈЃиЈЭдЄїи¶БдљУзО∞еЯОеЄВеТМеЖЬжЭСдєЛйЧігАВ2005еєідЄ≠еЫљеЖЬж∞СдЇЇеЭЗзЇѓжФґеЕ•дЄЇ3255еЕГдЇЇж∞СеЄБпЉМжѓФ2004еєіеҐЮйХњ6.2пЉЕпЉЫеЯОйХЗе±Еж∞СдЇЇеЭЗеПѓжФѓйЕНжФґеЕ•10493еЕГпЉМжѓФ2004еєіеҐЮйХњ9.6%пЉЫеЖЬжЭСжБ©ж†Ље∞Фз≥їжХ∞дЄЇ45.5%пЉМеЯОйХЗжБ©ж†Ље∞Фз≥їжХ∞дЄЇ36.7%пЉЫжМЙеєідЇЇеЭЗзЇѓжФґеЕ•дљОдЇО683еЕГзЪДж†ЗеЗЖпЉМ2005еєіжЬЂеЖЬжЭСиіЂеЫ∞дЇЇеП£дЄЇ2365дЄЗдЇЇпЉМжѓФ2004еєіжЬЂеЗПе∞С245дЄЗдЇЇгАВдї•дЄКжХ∞жНЃжШЊз§ЇпЉМеЯОеЄВеТМеЖЬжЭСдєЛйЧізЪДжФґеЕ•еЈЃиЈЭиЊЊеИ∞3.22еАНгАВ
еЬ®жФєйЭ©еЗЇзО∞еЫ∞йЪЊзЪДжЧґеАЩпЉМдЇЇдїђжАїдЉЪеЗЇзО∞дЄАзВєзХЩењµињЗеОїзЪДжГЕеЖµпЉМвАЬеЈ¶вАЭињЩзІНдє†жГѓжАІеКњеКЫеПИеЖТеЗЇжЭ•пЉМиЃ§дЄЇжФєйЭ©ињЭиГМдЇЖз§ЊдЉЪдЄїдєЙзЪДеОЯеИЩпЉМиЃ§дЄЇеЄВеЬЇеМЦдЊµзКѓдЇЖеЉ±еКњзЊ§дљУзЪДеИ©зЫКгАВзКєе¶ВељУеєіжЦЗйЭ©дЄАиИђпЉМжККдЄУеЃґе≠¶иАЕйГљжИідЄКдЇЖвАЬзЊОеЫљдЄ≠жГЕе±АеЖЕеЇФвАЭзЪДеЄље≠РпЉМиѓізїІзї≠жФєйЭ©дЉЪ襀вАЬи•њеМЦвАЭпЉМ襀вАЬеТМеє≥жЉФеПШвАЭгАВжЬЙдЇЇиЃ§дЄЇжФєйЭ©дЄНеИ∞дљНпЉМжЬЙдЇЇиЃ§дЄЇвАЬз≤ЊиЛ±вАЭеИґйА†дЇЖеБЗжФєйЭ©гАВжАОдєИиІ£еЖ≥жФєйЭ©дЄ≠еЗЇзО∞зЪДйЧЃйҐШпЉМйЭ†ињРеК®жЭ•иІ£еЖ≥пЉЯйЭ†еПНеП≥иГљиІ£еЖ≥пЉЯйЭ†жЙєеИ§зІБжЬЙеМЦеТМеЄВеЬЇеМЦпЉМиГљиІ£еЖ≥йЧЃйҐШеРЧпЉЯ
жИСдЄНзЯ•йБУвАЬжФєйݩ姱賕聯вАЭжШѓжАОдєИеЊЧеЗЇжЭ•зЪДгАВе¶ВжЮЬдїЕдї•жХЩиВ≤гАБеМїзЦЧзЪДжФєйЭ©иЃЇжИРиі•пЉМињЩжЧ†зЦСжШѓдЄАдЄ™ж≤°жЬЙеЕ®е±АиІВзЪДиЃЇи∞ГгАВињЩдЇЫвАЬжЦ∞еЈ¶жіЊвАЭжАОдєИеПѓдї•жЧ†иІЖ13дЇњдЇЇеП£дЊЭйЭ†иЗ™еКЫжЫізФЯиІ£еЖ≥еРГй•≠з©њи°£пЉМеєґеЬ®2003еєіињИињЗдЇЇеЭЗGDP1000зЊОеЕГе§ІеЕ≥ињЩдЄ™дЇЛеЃЮгАВеЕґжђ°пЉМжФєйЭ©еЉАжФЊдї•еЙНзїЭеѓєиіЂеЫ∞дЇЇеП£жШѓ2.5дЇњдЇЇпЉМиіЂеЫ∞дЇЇеП£ељУжЧґжШѓ4дЇњпЉМеН†еЫЫеИЖдєЛдЄАпЉМ2005еєіжЬЂеЖЬжЭСиіЂеЫ∞дЇЇеП£дЄЇ2365дЄЗдЇЇпЉМеН†13дЇњдЇЇеП£зЪД1.81пЉЕгАВе∞љзЃ°еЬ®иіЂеѓМеЈЃиЈЭжЙ©е§ІзЪДжГЕеЖµдЄЛпЉМиіЂеЫ∞дЇЇеП£дєЯжШѓеЬ®йАРеєіеЗПе∞СпЉМдїЕеЬ®2005еєіеЖЬжЭСдЇЇеП£жѓФ2004еєіеЗПе∞С245дЄЗгАВдЄ≠е§ЃеЬ®жХідЄ™вАЬеНБдЄАдЇФвАЭжЬЯйЧізЪДйЗНзВєпЉМжШѓвАЬеїЇиЃЊжЦ∞еЖЬжЭСвАЭпЉМеЕґзЫЃзЪДпЉМе∞±жШѓеЬ®жЫіеЃљзЪДи¶ЖзЫЦйЭҐдЄКиІ£еЖ≥иіЂеѓМеЈЃиЈЭињЗе§ІзЪДйЧЃйҐШ,иАМдЄНжШѓзЇ†зЉ†еЬ®еЯОеЄВгАВйВ£дЇЫеЦЬ搥еЬ®зљСдЄКи∞ИиЃЇжФєйݩ姱賕зЪДдЇЇдїђпЉМдЄНи¶БењШиЃ∞дЄ≠еЫљеИ∞зО∞еЬ®ињШжЬЙ9дЇњдЇЇзФЯжіїеЬ®еЖЬжЭСгАВ
дЄЦзХМдЄКж≤°жЬЙеНБеЕ®еНБзЊОзЪДдЇЛпЉМдЄ≠еЫљжШѓињЩдєИе§ІзЪДеЫљеЃґпЉМжИСдїђеБЪзЪДжШѓеЙНдЇЇж≤°жЬЙеБЪињЗзЪДдЇЛпЉМеЫЇзДґжФєйЭ©еЗЇзО∞дЇЖдЄАдЇЫйЧЃйҐШпЉМдљЖжИСдїђдєЯдЄНиГљеЫ†еЩОеЇЯй£ЯпЉМдЄНиГљеБЬж≠•дЄНеЙНгАВеєґдЄФжИСдїђзЪДиГЖе≠РињШжЬЙе§ІдЄАзВєпЉМеП™жШѓеЬ®е§ДзРЖеЕЈдљУйЧЃйҐШжЧґи∞®жЕОдЄАзВєпЉМеПКжЧґжАїзїУзїПй™МгАВжАОдєИжАїзїУзїПй™МпЉЯеЬ®ињЩзІНеЃЮйЩЕйЬАи¶БдЄЛпЉМ2006еєі3жЬИ4жЧ•гАКдЄ≠еЫљеЃПиІВзїПжµОдЄОжФєйЭ©иµ∞еКњеЇІи∞ИдЉЪгАЛеПђеЉАпЉМињЩжШѓдЄАдЄ™зЇѓе≠¶жЬѓжАІиі®зЪДз†ФиЃ®дЉЪпЉМдЄНдї£и°®дЄ≠е§ЃзЪДеЖ≥з≠ЦгАВзљСзїЬдЄКжККињЩжђ°дЉЪиЃЃзІ∞дЄЇвАЬи•ње±±дЉЪиЃЃвАЭгАВ
вАЬдЄ≠еЫљеЃПиІВзїПжµОдЄОжФєйЭ©иµ∞еКњеЇІи∞ИдЉЪвАЭдЉЪйХњйЂШе∞ЪеЕ®еЬ®дЉЪиЃЃеЉАеІЛжЧґпЉМжПРеЗЇдЄЙдЄ™еїЇиЃЃпЉЪдЄАжШѓи¶БеїЇиЃЃиГ°жАїдє¶иЃ∞еЗЇжЭ•иЃ≤иѓЭпЉМиЃ≤дїАдєИпЉЯдЄїи¶БиЃ≤еПЈеПђеЕ®еЕЪгАБеЕ®еЫљдЇЇж∞СеЫҐзїУиµЈжЭ•пЉМеЭЪеЃЪдЄНзІїжРЮжФєйЭ©пЉМдЄАењГдЄАжДПи∞ЛеПСе±ХпЉМдЄНи¶БдЇЙиЃЇпЉМдЄНи¶БжРЮеИЖи£ВгАВжЙАдї•пЉМгАКдЇЇж∞СжЧ•жК•гАЛзЪДињЩзѓЗз§ЊиЃЇвАЬеНГеСЉдЄЗеФ§еІЛеЗЇжЭ•вАЭпЉЫдЇМжШѓеїЇиЃЃжЫіеК†еЕ≥ж≥®еЫ∞йЪЊзЊ§дљУпЉМзЉ©е∞ПиіЂеѓМдєЛйЧізЪДеЈЃиЈЭгАБдЄНеРМеЬ∞еМЇзЪДеЈЃиЈЭпЉЫдЄЙжШѓеїЇиЃЃеїЇзЂЛи∞ГиІ£дЄЇж†ЄењГзЪДз§ЊдЉЪжХіеРИжЬЇеИґпЉМзІѓжЮБз®≥嶕еЬ∞жО®ињЫжФњеЇЬдљУеИґжФєйЭ©пЉМеїЇзЂЛеИ©зЫКи°®иЊЊеТМеѓєиѓЭеНПеХЖдљУеИґпЉМеЉХеѓЉеРДдЄ™еИ©зЫКзЊ§дљУеРИзРЖеРИж≥ХзЪДи°®иЊЊеИ©зЫКиѓЙж±ВгАВ
вАЬи•ње±±дЉЪиЃЃвАЭзЪДдЄїи¶БиЃЃйҐШжЬЙеЫЫдЄ™пЉЪ1гАБеЃПиІВжФєйЭ©иµ∞еКњпЉЫ2гАБеЖЬж∞СеЬЯеЬ∞еТМеЖЬж∞СеЈ•з§ЊдЉЪдњЭйЪЬпЉЫ3гАБеМїзЦЧжФєйЭ©пЉЫ4гАБжХЩиВ≤жФєйЭ©гАВ
еЬ®еЃПиІВзїПжµОиµ∞еКњињЩдЄ™иЃЃйҐШзЪДиЃ®иЃЇдЄ≠пЉМзД¶зВєдЄїи¶БйЫЖдЄ≠еЬ®вАЬжШѓеР¶и¶БжФЊжЭЊеѓєдїЈж†ЉзЪДзЃ°еИґвАЭдЄКгАВеПНеѓєжФЊжЭЊдїЈж†ЉзЃ°еИґзЪДдЇЇиЃ§дЄЇињЩжШѓвАЬжЦ∞иЗ™зФ±дЄїдєЙвАЭпЉМдљЖдїАдєИжШѓвАЬжЦ∞иЗ™зФ±дЄїдєЙвАЭињЩдЄ™ж¶ВењµпЉМжЧ†ж≥ХиІ£йЗКпЉМдєЯиѓідЄНжЄЕгАВжЫіжЬЙе•љдЇЛиАЕињЮжФЊжЭЊеѓєдїАдєИзЪДвАЬзЃ°еИґвАЭйГљж≤°жРЮжЄЕж•ЪпЉМеЉ†еЖ†жЭОжИізЪДдє±жЙєдЄАйАЪгАВ
зЙ©дїЈйЧЃйҐШжШѓе±ЮдЇОеОЖеП≤йБЧзХЩйЧЃйҐШпЉМиѓізЫіжО•зВєе∞±жШѓвАЬиЃ°еИТзїПжµОвАЭйБЧзХЩдЄЛжЭ•зЪДгАВеЬ®иЃ°еИТзїПжµОдљУеИґдЄЛпЉМзЙ©дїЈйГљзФ±еЫљеЃґиІДеЃЪгАВжЧ©еЬ®1988еєіпЉМеЫ†дЄЇи¶БдЄНи¶БжФЊеЉАз≤Ѓй£ЯдїЈж†ЉдЇІзФЯињЗдЇЙиЃЇгАВељУжЧґеЫ†дЄЇз≤Ѓй£ЯжФґиі≠дїЈйХњжЬЯеЃЪеЊЧињЗдљОпЉМеЯОеЄВзЪДйФАеФЃдїЈеПИдЄНиГљжПРйЂШпЉМеѓЉиЗійФАеФЃдїЈж†ЉеАТжМВпЉМе∞±жШѓвАЬеАТиіійТ±вАЭгАВйВ£дєИеАТиіізЪДињЩйГ®еИЖи∞БжЭ•дє∞еНХпЉЯзФ±еЫљеЃґжЭ•и°•иіігАВињЩзІНињЭиГМдїЈеАЉиІДеЊЛзЪДеБЪж≥ХпЉМдЄАжЦєйЭҐдљњеЖЬж∞СзІѓжЮБжАІи∞ГеК®дЄНиµЈжЭ•пЉМеП¶дЄАжЦєйЭҐдљњеۚ側賥жФњиГМдЄКдЇЖеЊИе§ІзЪДеМЕ襱пЉМ1988еЙНеЫљеЃґжѓПеєізФ®дЇОи°•иіізЙ©дїЈзЪДеЉАжФѓиЊЊеИ∞еЗ†зЩЊдЇњеЕГгАВељУжЧґжФЊеЉАз≤Ѓй£ЯдїЈж†ЉжЧґпЉМжЫЊзїПеЗЇзО∞ињЗвАЬжКҐиі≠й£ОвАЭпЉМдљЖеРОжЭ•зЪДдЇЛеЃЮиѓБжШОпЉМзРЖй°ЇдЇЖз≤Ѓй£ЯдїЈж†ЉпЉМдљњеЖЬж∞СжПРйЂШзІНз≤ЃзІѓжЮБжАІпЉМдњГињЫдЇЖз≤Ѓй£ЯдЇІйЗПеҐЮеК†пЉМеєґж≤°жЬЙеЗЇзО∞з≤Ѓй£ЯдЊЫеЇФзЯ≠зЉЇзЪДжГЕеЖµгАВеИ∞дЇЖ96еєіпЉМз≤Ѓй£ЯзЪДдЇІйЗПдљњеЫљеЃґзЪДеОЯжЬЙзЪДз≤ЃдїУйГљдЄНе§ЯзФ®пЉМдЄНеЊЧдЄНдњЃеїЇжЦ∞зЪДз≤ЃдїУжЭ•еВ®е§ЗгАВеТ±дїђжЬ±иАБжАїиѓівАЬдЄ≠еЫљзЪДз≤Ѓй£ЯдЄНзФЯдЇІйГље§ЯеРГеНБеєівАЭињЩеП•иѓЭжЧґпЉМеЇХж∞ФеНБиґ≥гАВдєЯж≠£жШѓжЬЙдЇЖињЩж†ЈзЪДеЇХж∞ФпЉМжЙНиГљеЬ®и•њйГ®зОѓеҐГжБґеМЦзЪДеЬ∞еМЇеЃЮи°МвАЬйААиАХињШжЮЧвАЭпЉЪиАБзЩЊеІУеОЯжЭ•зЪДеЬ®еЭ°еЬ∞дЄКеЉАиНТзІНж§НзЪДз≤Ѓй£ЯпЉМйА†жИРж∞іеЬЯжµБ姱гАВдљЖжШѓдЄНзІНж§Нз≤Ѓй£ЯеПИдЄНиГљзФЯе≠ШгАВзЬЛиµЈжЭ•е•љеГПжШѓдЄ™дЄ§йЪЊйЧЃйҐШпЉМдљЖжШѓж≠£жШѓеЫљеЃґжЬЙдЇЖз≤Ѓй£ЯпЉМжЙНдљњвАЬйААиАХињШжЮЧвАЭињЩдЄ™еЃПдЉЯзЪДиЃ°еИТеЊЧдї•еЃЮжЦљгАВеЖЬж∞СдЄНзїІзї≠еЬ®ж∞іеЬЯжµБ姱зЪДеЭ°еЬ∞дЄКзІНж§Нз≤Ѓй£ЯпЉМиАМжШѓзІН??дЇІйЗПзЫіжО•и°•иііз≤Ѓй£ЯгАВ
1988еєіжФЊеЉАз≤Ѓй£ЯдїЈж†ЉпЉМеЄ¶жЭ•з≤Ѓй£ЯеҐЮдЇІгАБдЄЇж≤їзРЖзОѓеҐГжПРдЊЫзЙ©иі®жФѓжМБдЄ§е§ІзЫКе§ДгАВж≠£е•љжЬЙдЄ™зљСеПЛжЫЊзїЩжИСжПРиµЈињЗпЉЪжЬЙдЄ™е≠¶иАЕжЬђжЭ•жШѓи¶БеИ∞и•њйГ®еЃ£дЉ†зОѓдњЭзЪДпЉМеПѓжШѓељУдїЦйЭҐеѓєзЭАж≤°й•≠еРГзЪДе≠©е≠РеЬ®жМЦж§Н襀зЪДжЧґеАЩ,дїЦеЃЮеЬ®иѓідЄНеЗЇеП£и¶БдњЭжК§зФЯжАБеє≥и°°гАВзЫЃеЙНзЪДзФЯе≠ШйЬАи¶БдЄОйХњжЬЯзЪДдњЭжК§зОѓеҐГдєЛйЧіжШѓжЬЙзЯЫзЫЊгАВиІ£еЖ≥ињЩдЄ™зЯЫзЫЊзЪДеКЮж≥Хе∞±жШѓпЉЪжЧҐи¶БеРГй•≠пЉМдєЯи¶БдњЭжК§зОѓеҐГгАВињЩе•љеГПжЬЙзВєеЉЇдЇЇжЙАйЪЊгАВдљЖжШѓж≠£жШѓжФЊжЭЊеѓєдЄАдЇЫињЭиГМдїЈеАЉиІДеЊЛдЇЛзЙ©зЪДзЃ°еИґпЉМжЙНдљњеЊЧжИСдїђжЬЙзЙ©иі®еКЫйЗПеОїиІ£еЖ≥ињЩдЄ™вАЬеЉЇдЇЇжЙАйЪЊвАЭзЪДйЧЃйҐШгАВињЩе∞±жШѓжФЊеЉАдїЈж†ЉеѓєеЃПиІВзїПжµОеЄ¶жЭ•зЪДзЫКе§ДгАВ
ињСеєіжЭ•пЉМиіЂеѓМеЈЃиЈЭжЙ©е§ІдЇЖпЉМдљЖеЬ®иІ£еЖ≥иіЂеѓМеЈЃиЈЭињЗе§ІзЪДдЇЙиЃЃдЄ≠пЉМ襀жЛњжЭ•дљЬжѓФиЊГзЪДжШѓдЄ§зІНж®°еЉПпЉМдЄАжШѓиЛПеЈЮж®°еЉПпЉМдЇМжШѓжЄ©еЈЮж®°еЉПгАВињЩдЄ§зІНж®°еЉПпЉМеЃШжЦєеТМе≠¶зХМеРДжЬЙеРДзЪДзЬЛж≥ХпЉМиАБзЩЊеІУдєЯеЖЈжЪЦиЗ™зЯ•гАВиЛПеЈЮзїПжµОеПСе±ХзЪДзЙєзВєеЬ®дЇОпЉЪеИЫйА†дЇЖGDPеҐЮйХњзЪДвАЬз•ЮиѓЭвАЭпЉМдљњеЊЧжФњеЇЬжЬЙеЊИеЉЇзЪД賥еКЫжФєеЦДеЯЇз°АиЃЊжЦљеїЇиЃЊпЉМдљЖиЛПеЈЮжЩЃйАЪеЄВж∞СжФґеЕ•еҐЮйХњзЉУжЕҐпЉМеЬЯеЬ∞иµДжЇРеЗПе∞СпЉМж∞СжЧПеУБзЙМйАРжЄРжЈ°еЗЇпЉМвАЬдЄЦзХМеЈ•еОВвАЭиЇЂдїљиґКжЭ•иґКеЉЇпЉМжИРдЄЇдЄАзІНиЛПеЈЮвАЬеЉЇжФњеЇЬеЉ±з§ЊдЉЪвАЭзЪДзО∞и±°пЉЫжЄ©еЈЮеОЖжЭ•жШѓвАЬиЧПеѓМдЇОж∞СвАЭпЉМиЩљзДґжЄ©еЈЮGDPеП™жШѓиЛПеЈЮзЪД1/3пЉМдљЖеЯОеЄВе±Еж∞СдЇЇеЭЗжФґеЕ•еНіжШѓиЛПеЈЮзЪД1.2еАНпЉМеЖЬжЭСе±Еж∞СзЪДињЩй°єжХ∞е≠ЧеИЩзЫЄељУдЇОеРОиАЕзЪД80%гАВйЧЃйҐШжШѓпЉЪжЄ©еЈЮзЪДеЯЇз°АиЃЊжЦљеїЇиЃЊињЬ赴дЄНдЄКиЛПеЈЮгАВжАОдєИиІ£еЖ≥жФњеЇЬ賥еКЫеТМз§ЊдЉЪзЊ§дљУдєЛйЧіжФґеЕ•еИЖйЕНзЪДйЧЃйҐШпЉМеПИжШѓдЄАдЄ™зЯЫзЫЊгАВеЬ®ињЩзІНзЯЫзЫЊдЄЛпЉМдЄНеЊЧдЄНдљЬеПИеЗЇдЄАдЄ™вАЬеЉЇдЇЇжЙАйЪЊвАЭзЪДеЖ≥з≠ЦпЉМе∞±жШѓвАЬжФњеЇЬзЪДжФґеЕ•и¶БеҐЮеК†пЉМз§ЊдЉЪзЊ§дљУзЪДжФґеЕ•дєЯи¶БеҐЮеК†вАЭгАВињЩж†ЈдЄАжЭ•пЉМдЄНеЊЧдЄНи∞ГжХіжФґеЕ•еИЖйЕНжЬЇеИґпЉМжАОдєИи∞ГиКВпЉЯињЩе∞±и¶БиАГиЩСжФњеЇЬеТМеЄВеЬЇдєЛйЧізЪДеЕ≥з≥їгАВ
дљЖжШѓиЛПеЈЮж®°еЉПдЄОжЄ©еЈЮж®°еЉПдєЛйЧізЪДжѓФиЊГиГљдЄНиГљдљЬдЄЇдї£и°®жАІзЪДжѓФиЊГпЉЯжШЊзДґжШѓдЄНиГљзЪДгАВйБУзРЖеЊИзЃАеНХпЉМињЩдЄ§зІНж®°еЉПйГљжШѓжККзїПжµОеПСиЊЊеЬ∞еМЇжЛњжЭ•дљЬжѓФиЊГпЉМењљиІЖдЇЖдЄЬгАБи•њйГ®еЬ∞еМЇеЈЃиЈЭињЩдЄ™жЫіеЃПиІВеЯЇз°АгАВеЫ†ж≠§еЬ®иАГиЩСиІ£еЖ≥иіЂеѓМеЈЃиЈЭзЪДйЧЃйҐШдЄКпЉМжЫіе§ЪзЪДжШѓи¶БиІ£еЖ≥дЄЬи•њйГ®еЬ∞еМЇеЈЃиЈЭгАБеЖЬжЭСеТМеЯОеЄВдєЛйЧізЪДеЈЃиЈЭзЪДйЧЃйҐШгАВеЕ®еЫљеЯЇе∞Љз≥їжХ∞дЄКеНЗйЗМйЭҐжЬЙ30%-50%зЪДеЫ†зі†жШѓдЄОеЬ∞еМЇеЈЃиЈЭзЫЄеЕ≥зЪДпЉМе∞±жШѓзФ±дЇОеРДеЬ∞зЪДеПСе±Хж∞іеє≥дЄНдЄАж†ЈгАВжИСдїђжЬЙдЄАйГ®еИЖзЪДжФґеЕ•еИЖйЕНзЪДеЈЃиЈЭжШѓеЕ®зРГеМЦеЄ¶жЭ•зЪДгАВйЂШзЇІзЩљйҐЖзЪДеЈ•иµДеєіиЦ™иЊЊеИ∞дЄАзЩЊдЄЗпЉМдїЦе∞±жШѓдЄАдЄ™еК≥еК®иАЕпЉМеЈ•иЦ™йШґе±ВпЉМиЊЊеИ∞дЇЖдЄАзЩЊдЄЗпЉМзФЪиЗ≥жЫійЂШзЪДгАВжЩЃйАЪзЪДдЄАдЄ™еК≥еК®иАЕеИґйА†дЄЪдЄАеєіињШдЄНеИ∞дЄАдЄЗпЉМзЫЄељУдЇОдЄАзЩЊеАНгАВжЙАдї•еЊИе§Ъе§Іе≠¶жѓХдЄЪзФЯеѓєвАЬе§ЦдЉБвАЭжГЕжЬЙзЛђйТЯпЉМињЩдЄ≠йЧіе∞±жЬЙдЄАдЄ™еИ©зЫКй©±дљњзЪДйЧЃйҐШгАВи∞ГиКВињЩдЇЫеЈЃиЈЭдЄНиГљйЗЗзФ®вАЬеПЦжґИињЩдЇЫдЇЇжФґеЕ•вАЭињЩдЄ™еКЮж≥ХпЉМеП™иГљдЊЭйЭ†з®ОжФґпЉМињЩеПИзЙµжЙѓеИ∞еЃПиІВеЖ≥з≠ЦпЉМжЙАдї•еЙНжЃµжЧґйЧіи∞ГйЂШдЇЖдЄ™дЇЇжЙАеЊЧз®ОеЊБжФґиµЈзВєпЉМдљЖеѓєдЄ™дЇЇжЙАеЊЧз®ОиµЈзВєиГљдЄНиГљдЄАдЄЛеЃЪеЊЧињЗйЂШпЉЯдЄНиГљпЉМеЫ†дЄЇз®ОжФґињЗйЂШпЉМйЂШжКАиГљзЪДдЇЇдЉЪзІїж∞СпЉМиЈСдЇЖпЉМдЄНеСЖеЬ®ињЩпЉМйА†жИРдЇЇжЙНзЪДжµБ姱гАВ
жИСдїђдєЯеПѓдї•и¶Бж±ВеҐЮеК†дљОеЈ•иµДж∞іеє≥еК≥еК®иАЕзЪДжФґеЕ•пЉМдљЖдЉЪжЬЙдїАдєИзїУжЮЬпЉЯдЉБдЄЪзЪДжФґзЫКжЙњеПЧдЄНдЇЖйЂШеЈ•иµДпЉМдЉБдЄЪдЉЪеЮЃжОЙпЉМи∞БйГљж≤°й•≠еРГгАВе§ЦиµДдЉБдЄЪдєЯиЈСеИ∞еЕґдїЦеЫљеЃґдЇЖгАВйВ£дЄ™жЧґеАЩдЄНиГљзІїж∞СзЪДпЉМеП™иГљжШѓеЯОеЄВзЪДз©ЈдЇЇеТМеЖЬж∞СпЉМдЄ≠еЫљжИРдЄЇдЄАдЄ™зЬЯж≠£зЪДвАЬз©ЈдЇЇеЫљвАЭгАВиІ£еЖ≥иіЂеѓМеЈЃиЈЭдЄНжШѓдЄАиєіиАМе∞±зЪДдЇЛпЉМењЕй°їи¶БдїОжЬАж†єжЬђгАБжґЙеПКйЭҐжЬАеєњзЪДеЬ∞жЦєеЉАеІЛгАВ
еѓєдЇОиіЂеѓМеЈЃиЈЭеЄ¶жЭ•зЪДз§ЊдЉЪељ±еУНпЉМеЬ®вАЬи•ње±±дЉЪиЃЃвАЭдЄКпЉМе≠¶иАЕе≠ЩзЂЛеє≥еБЪдЇЖдЄАдЄ™иііеИЗзЪДжАїзїУпЉМдїЦиЃ§дЄЇзЫЃеЙНзЪДеИЖж≠ІжЬЙдЄЙзВєпЉЪ
зђђдЄАжШѓжИСдїђдїОжДПиѓЖ嚥жАБжИЦиАЕжФњж≤їеЖ≥еЃЪдЄАеИЗзЪДжЧґдї£пЉМињЫеЕ•еИ©зЫКжЧґдї£зЪДжЧґеАЩпЉМдљЖжИСдїђзЪДжАЭзїіеТМиѓ≠и®Аж≤°жЬЙиЈЯдЄКпЉМињЩжШѓеЊИйЗНи¶БзЪДдЄАдЄ™еОЯеЫ†пЉЫ
зђђдЇМдЄ™еОЯеЫ†жШѓзїУжЮДеЫ†зі†пЉМдЄКе±Веѓ°е§іеМЦпЉМдЄЛе±Вж∞Сз≤єеМЦпЉМдЄ•йЗНзЪДдЄ§жЮБеИЖеМЦгАВжѓФе¶ВзљСеПЛиГ°зђ≥еНБдєЭжЛНеЙН姩еПСдЇЖдЄ™иііпЉМиѓіжЯРдЇЫз©ЈдЇЇеПИеПѓжБ®дєЛе§ДпЉМиѓізЪДеАТжШѓдЇЛеЃЮпЉМеП™дЄНињЗдЄАеП£дЄАдЄ™з©ЈдЇЇпЉМзЬЛеЊЧи∞БйГљйђЉзБЂзїњпЉМдљЖжШѓжخ姩жЬЙдЇЇеПСеЗЇеПНй©≥дїЦзЪДеЄЦе≠РдєЯдЄНе∞±иІБеЊЧе∞±жШѓеѓєзЪДпЉМдЄАдЄ™жО•дЇМињЮдЄЙдЄНйБµеЃИзЃ°зРЖиІДеЃЪзЪДдЇЇдЄЇдїАдєИдЉЪжЬЙдЇЇжФѓжМБпЉМињЩе∞±жШѓжА™зО∞и±°гАВињЩдЄ§дЄ™еЄЦе≠РдєЛйЧізЪДеПНеЈЃжЈ±еИїзЪДиѓіжШОзЫЃеЙНдЄ§жЮБеИЖеМЦзЪДз®ЛеЇ¶пЉЫ
зђђдЄЙдЄ™еОЯеЫ†жШѓжФњеЇЬеТМеЄВеЬЇзЪДеАТжМВпЉМзїПжµОдљУеИґеТМеЄВеЬЇзЪДдљЬзФ®еЇФиѓ•жШѓзЫЄеПНзЪДпЉМеЄВеЬЇйА†жИРдЄНеє≥з≠ЙпЉМзїПжµОдљУеИґжЭ•еЉ•и°•дЄНеє≥з≠ЙпЉМдљЖжШѓзО∞еЬ®дЄ§иАЕдєЛйЧізЪДеЕ≥з≥їж≤°жРЮжЄЕпЉМињЩе∞±зЙµжЙѓеИ∞ж≥ХеЊЛеТМеРДдЄ™йГ®йЧ®иБМиГљиБМиі£зХМеЃЪзЪДйЧЃйҐШгАВ
еЖЬж∞СеЬЯеЬ∞йЧЃйҐШгАВеЖЬдЄЪз®ОеПЦжґИдєЛеРОпЉМеЖЬдЄЪе§ІзЬБгАБеЖЬдЄЪе§ІеОњзЪД賥еКЫжАОдєИиІ£еЖ≥пЉЯеРДжЦєйГљжККзЫЃеЕЙйЫЖдЄ≠еЬ®еЬЯеЬ∞дЄКпЉМжФєеПШеЬЯеЬ∞еЇФзФ®дї•еПКеАЯеЬ∞зФЯ賥пЉМдљЖжШѓеЖЬж∞СжЧ†ж≥ХдњЭйЪЬпЉМињЩжШѓеЊИе§ЪзЪДеЬ∞жЦєеЫ∞еҐГгАВеПЦжґИеЖЬдЄЪз®ОпЉМзЯ≠жЧґйЧіеЖЕжККеЖЬжЭСеЊИе§ЪйЧЃйҐШжЪійЬ≤еЗЇжЭ•пЉМдљњеЊЧеЖЬжЭСеТМеРДжЦєйЭҐжФєйЭ©ињЂдЄНеЃєзЉУгАВеЖЬдЄЪе§ІзЬБеТМеЖЬдЄЪе§ІеОњи¶БиІ£еЖ≥賥еКЫйЧЃйҐШпЉМеП™жЬЙеПСе±ХеЈ•дЄЪпЉМйЬАи¶БеЬЯеЬ∞пЉМдњЭйЪЬз≤Ѓй£ЯеЃЙеЕ®дєЯйЬАи¶БеЬЯеЬ∞гАВињЩжШѓжФєйЭ©дЄ≠еЗЇзО∞зЪДзђђдЄЙдЄ™вАЬдЄ§йЪЊвАЭгАВеПСе±ХдЄОзФЯе≠Ши∞Биљїи∞БйЗНпЉМињШзЬЯзЪДдЄНе•љиѓігАВдЄНеПСе±ХпЉМйЭҐдЄіиіЂеЫ∞пЉЫи∞ЛеПСе±ХпЉМеПѓиГљз≤Ѓй£ЯеЃЙеЕ®жЧ†ж≥ХдњЭйЪЬгАВеЖЬж∞СзЪДеЕ≥ењГзЪДжШѓеЬЯеЬ∞иљђиЃ©йЗСеТМ姱еОїеЬЯеЬ∞еРОзЪДзФЯе≠ШйЧЃйҐШгАВеЬЯеЬ∞жШѓеЫљеЃґжЬЙзЪДпЉМеЬЯеЬ∞иљђиЃ©йЗСеЇФиѓ•ељТдЇОеЫљеЃґињШжШѓељТдЇОз§ЊдЉЪпЉЯињЩжШѓжЧІдљУеИґзХЩдЄЛжЭ•зЪДйЧЃйҐШгАВе¶ВжЮЬиљђиЃ©йЗСељТдЇОз§ЊдЉЪпЉМе∞±йЭҐдЄіжЙњиЃ§еЬЯеЬ∞зІБжЬЙеМЦпЉМе¶ВжЮЬељТеЫљеЃґпЉМеЖЬж∞СзЪДеИ©зЫКеТМеЫљеЃґеИ©зЫКе∞±дЇІзФЯеЖ≤з™БгАВжККеЬЯеЬ∞еҐЮеАЉзХЩзїЩжИРдЇ§зЪДеЖЬж∞СпЉМдљњдїЦдїђжЪіеѓМзФЯжіїпЉМињЩдєЯдЄНзђ¶еРИз§ЊдЉЪзЪДеЕђеЕ±еОЯеИЩгАВињЩе∞±жШѓвАЬжЙУеЈ¶иљђеЉѓзБѓеРСеП≥иљђвАЭпЉМеРНдЄНж≠£и®АдЄНй°ЇгАВзЫЃеЙНзЪДе§ДзРЖжЦєж≥ХпЉМеП™жШѓеЬ®еЬЯеЬ∞еҐЮеАЉжФґзЫКдЄ≠зїЩеЖЬж∞Си°•еБњгАБе∞±дЄЪжЬЇдЉЪгАВеЬ®еЈ•дЄЪеМЦињЫз®ЛдЄ≠пЉМжЫіе§ЪзЪДеЖЬж∞С姱еОїеЬЯеЬ∞жШѓжЧ†ж≥ХйБњеЕНзЪДдЇЛпЉМжАОдєИзїЩеЖЬж∞СзФЯе≠ШжЭГгАБеПСе±ХжЭГпЉМжШѓвАЬи•ње±±дЉЪиЃЃвАЭзЪДеП¶дЄАдЄ™зД¶зВєгАВињЩдЇЫйЧЃйҐШзЪДдЇІзФЯпЉМжЬЙдЄ§дЄ™йЗНе§ІеОЯеЫ†пЉМдЄАжШѓдЇЇеП£йЧЃйҐШпЉЫдЇМжШѓдЇІжЭГйЧЃйҐШпЉМвАЬжЙАжЬЙжЭГвАЭеТМвАЬдљњзФ®жЭГвАЭеєґе≠ШпЉМи∞БзЪДеИ©зЫКеН†дЄїдљУпЉЯжФєйЭ©жЬђжЭ•е∞±жШѓдЄАеЬЇжЦ∞гАБжЧІеИ©зЫКзЊ§дљУдєЛйЧізЪДеЖ≤з™БпЉМињЩеЬЯеЬ∞йЧЃйҐШдЄКпЉМжШѓжККеИ©зЫКдЇ§зїЩеЫљеЃґињШжШѓдЇ§зїЩз§ЊдЉЪпЉЯињЩдЄ™йЧЃйҐШеЬ®еЯОеЄВдєЯжЬЙз±їдЉЉжГЕеЖµпЉМжѓФе¶ВжИње±ЛдЇІжЭГпЉМдљ†дє∞дЇЖжИњпЉМдљЖжШѓжЛ•жЬЙеЊЧ姱вАЬдљњзФ®жЭГвАЭпЉМиАМдЄНжШѓвАЬжЙАжЬЙжЭГвАЭгАВжЙАдї•иѓігАКзЙ©жЭГж≥ХгАЛзЪДдЇІзФЯжШѓеКњеЬ®ењЕи°МпЉМдєЯжШѓиІ£еЖ≥еИ©зЫКеИЖйЕНзЪДдЄАдЄ™ж≥ХеЊЛдЊЭжНЃгАВ
еМїзЦЧжФєйЭ©йЧЃйҐШгАВеМїзЦЧжФєйЭ©йЧЃйҐШйЫЖдЄ≠дљУзО∞еЬ®вАЬзЬЛзЧЕиіµвАЭдЄКйЭҐгАВжХідЄ™еМїзЦЧдљУз≥їеМЕжЛђеМїзЦЧдњЭйЩ©гАБеМїзЦЧжЬЇжЮДзЃ°зРЖдљУеИґгАБиНѓеУБзФЯдЇІжµБйАЪдЄЙдЄ™жЦєйЭҐгАВињЩдЇЫзОѓиКВйЗМжЬАйЪЊе§ДзРЖзЪДжШѓвАЬйГ®йЧ®еИ©зЫКвАЭгАВеЬ®зљСзїЬдЄК襀姲жЙєзЙєжЙєзЪДеЉ†зїіињОжЈ±еИїзЪДжП≠з§ЇдЇЖйГ®йЧ®еИ©зЫКпЉЪвАЬеЗ†еєіеЙНжИСе∞±иЃ≤ињЗпЉМеЕЂеНБеєідї£зЪДжФєйЭ©жЬЙеЊИе§ІзЪДпЉМдљУжФєеІФиЃ°еИТзїПжµОж≤°жЬЙзЛђзЂЛдљУпЉМжЙАдї•жЛЉеСљзЪДи¶БжФєйЭ©пЉМжЙАдї•пЉМдїЦжИРдЄЇдЄАдЄ™дљУжФєйГ®йЧ®жКЧи°°зЪДеКЫйЗПпЉМ聰賥йГ®йЧ®жПРеЗЇжЭ•зЪДйЧЃйҐШдїЦдїђйГљеПѓдї•жКЧи°°пЉМиАМ聰賥йГ®йЧ®ж≤°жЬЙзЪДиѓЭпЉМе∞±жШѓжѓПдЄ™йГ®йЧ®иЗ™еЈ±зЪДжЭГеИ©зЪДйЧЃйҐШгАВжЙАдї•пЉМзО∞еЬ®жЬЙдЄАдЄ™жАїдљУжФєйЭ©е∞±еЊИйЪЊдЇЖгАВжЙАдї•пЉМзО∞еЬ®жШѓеЊИеН±йЩ©зЪДгАВе¶ВжЮЬзЬЯж≠£зЪДи¶БжЬЙдЄАдЄ™жФєйЭ©зЪДеЉХеѓЉеКЫпЉМе∞±еЇФиѓ•жЬЙдЄАдЄ™еЊИеЉЇзЪДзП≠е≠РпЉМдЄУйЧ®иІДеИТгАВдїїдљХзЪДжФєйЭ©зЪДдїїеК°ж≤°жЬЙеЃМжИРпЉМжФєйЭ©зЪДжЬЇжЮДе∞±ељїжОЙдЇЖвАЭгАВйГ®йЧ®еИ©зЫКзЪДеЖ≤з™БдљњеЊЧжЙІи°МжФєйЭ©зЪДжЬЇжЮДеЬ∞дљНе∞іе∞ђпЉМдљ†дЄНжШѓи¶БжФєпЉЯжИСжККдљ†жТ§дЇЖзЬЛдљ†ињШжЛњдїАдєИжФєпЉЯ
жХЩиВ≤жФєйЭ©дЄ≠пЉМжЬЙдЄ§дЄ™жµБ姱пЉМдЄАжШѓеЄИиµДжµБ姱пЉМдЇМжШѓе≠¶зФЯзЪДзФЯжЇРжµБ姱гАВе•љжХЩеЄИеИ∞еЫље§ЦпЉМе•ље≠¶зФЯдєЯеИ∞еЫље§ЦпЉМдЄЇдїАдєИдЄ≠еЫљзЪДе≠¶зФЯзГ≠и°ЈеЗЇеЫљзХЩе≠¶пЉМзФЪиЗ≥дЄ≠е≠¶зФЯеП™и¶БжЬЙжЬЇдЉЪдєЯи¶БеЗЇеЫљпЉЯињЩдЄ™йЧЃйҐШжФїеЗїжХЩиВ≤жФєйݩ姱賕зЪДдЇЇйЧ≠еП£дЄНжПРпЉМе§ІеЃґеП™еЕ≥ењГе≠¶иієпЉМзљСдЄКе∞±еП™дЉ†дЄАеП•иѓЭвАЬз©ЈдЇЇдЄКдЄНиµЈе§Іе≠¶пЉМеЫ†дЄЇе≠¶иієе§™дљОвАЭпЉМж≤°жЬЙдЇЇеЕ≥ењГжАОдєИеїЇиЃЊдЄАжЙАе•љзЪДе§Іе≠¶гАВи¶БзХЩдљПжХЩеЄИпЉМењЕй°їжЬЙе•љзЪДеЊЕйБЗпЉМи¶БзХЩдљПе≠¶зФЯпЉМењЕй°їжПРдЊЫе•љзЪДжХЩиВ≤пЉМе•љзЪДиЃЊжЦљгАВеЫљеЃґжШѓж≤°жЬЙзїЩйТ±зЪДпЉМе≠¶ж†°и¶БењЕй°їиЗ™еЈ±жГ≥еКЮж≥ХгАВеЉ†зїіињОжШѓиѓідЇЖвАЬз©ЈдЇЇдЄКдЄНиµЈе§Іе≠¶пЉМеЫ†дЄЇе≠¶иієе§™дљОвАЭињЩеП•иѓЭпЉМдљЖжШѓињЩеП•иѓЭзЪДдЊЭжНЃжШѓпЉЪжИСдїђзФ®дљОе≠¶иієзЪДеКЮж≥ХйГљжШѓи°•иііпЉМиАМдЄНжШѓи°•зїЩз©ЈдЇЇпЉМжИСдїђе¶ВжЮЬиІДеЃЪе≠¶иієе§Ъе∞СзФ®дЇОз©ЈдЇЇеК©е≠¶йЗСпЉМињЩдЇЫйЧЃйҐШе∞±еПѓдї•еЊИе•љзЪДиІ£еЖ≥гАВињЩдЄ™дЊЭжНЃеЬ®гАКи•ње±±дЉЪиЃЃзЇ™и¶БгАЛйЗМжЧґеПѓдї•жЯ•еЊЧеИ∞зЪДгАВ
иМЕдЇОиљЉжМЗеЗЇпЉЪеЬ®жФєйЭ©зЪДињЫз®ЛдЄ≠еПСзФЯдЇЖиЃЄе§ЪеЫ∞йЪЊпЉМзЙєеИЂжШѓеЄХйЫЈжЙШжФєињЫзЪДжЬЇдЉЪеЈ≤зїПзФ®е∞љпЉМжФєйЭ©еЉАеІЛжНЯеЃ≥жЯРйГ®еИЖдЇЇзЪДеИ©зЫКжЧґпЉМеѓєжФєйЭ©зЪДжЦєеРСеТМзЫЃж†ЗжПРеЗЇдЇЖжААзЦСгАВињЩе∞±жШѓељУеЙНжИСеЫљжФєйЭ©жЙАйЭҐдЄізЪД嚥еКњгАВзФ±дЇОиіЂеѓМеЈЃиЈЭжЙ©е§ІпЉМеЈ•еЖЬе§ІдЉЧзЪДжФґеЕ•еҐЮеК†еєЕеЇ¶дЄНе§ІпЉМиЕРиі•йЧЃйҐШж≤°жЬЙжШОжШЊе•љиљђпЉМиАМи±™еѓМдїђжМ•йЬНжµ™иієпЉМз§ЊдЉЪдЄНеЕђжШОжШЊжЪійЬ≤гАВињЩжЧґеАЩиЃЄе§ЪдЇЇеѓєжФєйЭ©зЪДзЫЃж†ЗжДЯеИ∞жААзЦСпЉЪжШѓдЄНжШѓжИСдїђиµ∞йФЩдЇЖиЈѓпЉМиѓ•дЄНиѓ•еЊАеЫЮиµ∞пЉМињЗдЄАдЄ™жѓФиЊГеє≥еЭЗзЪДжЧ•е≠РпЉЯињЩжЧґеАЩзЫЃж†ЗзЪДйЗНи¶БжАІйЗНжЦ∞жШЊйЬ≤гАВеИ∞еЇХжШѓзЫЃж†ЗйФЩдЇЖињШжШѓињЗз®ЛдЄ≠зЪДйЧЃйҐШпЉЯеѓєдЄїжµБзїПжµОе≠¶еЭЪдњ°зЪДдЇЇдЉЪдЄїеЉ†еОЯжЭ•зЪДжФєйЭ©жЦєеРСпЉМеєґжМЗеЗЇйЧЃйҐШжШѓж≥Хж≤їзЪДжЭЊеЉЫпЉЫж≤°жЬЙж≥Хж≤їзЪДеЄВеЬЇе∞ЖжШѓжЛЙзЊОеЉПзЪДпЉМеЭПзЪДеЄВеЬЇзїПжµОгАВ
6жЬИ5жЧ•пЉМгАКдЇЇж∞СжЧ•жК•гАЛињЩзѓЗзљ≤еРНжЦЗзЂ†еЖНжђ°зїЩжФєйЭ©еЃЪдЇЖеЯЇи∞ГпЉЪжФєйЭ©жЦєеРСдЄНдЉЪеПШпЉМжОТйЩ§дЄАиµЈйШїеКЫдєЯи¶БжККжФєйЭ©ињЫи°МеИ∞еЇХгАВ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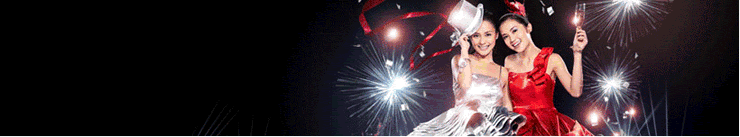
 |Archiver|mobile|The little black house|Shanghai WTO Net
( ж≤™ICPе§З10034107еПЈ-3 )
|Archiver|mobile|The little black house|Shanghai WTO Net
( ж≤™ICPе§З10034107еПЈ-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