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幸之父”故里,没落的皇家茶园 文 胡同 除非有测速拍照,老六几乎一路都在飙车。在距离目的地不到100公里的地方,他还是被警察拦进了服务区,扣6分,罚款100元。 这是3月27日,为赶晚饭,老六凌晨5点多就从广州开车出发,等他赶到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上凤溪村,时针已经转了一圈。 小古这天也起个大早,为了采到清明节前的、头一批发芽的荒野茶。人手不够的时候,他不得不背着竹篓上山,看到有冒尖的,就自己动手。 小古到一个村子收茶。 从唐宋时期开始,屏南就是献给皇家的天山贡茶和北苑贡茶的产区。只是,这种历史色彩在今天的商业上难以变现,人们更青睐叫得出名字的茶,比如正山小种、武夷大红袍、纯料生普;哪怕不懂茶的人,也可以对“喜茶”、“茶颜悦色”这些快消茶饮如数家珍。反观屏南,就算地道的屏南人,都没法马上说出当地最有名的是什么茶。 正是因为处在这样的尴尬境地,老六才觉得屏南茶极具性价比,能以自己可承受的价格买下这些绝好的茶叶。这是他来屏南收茶的第五年了。 将芽头挑出来,做成银尖。好茶注定是讲究产地和工艺的。 皇家茶园 老六正在进行他的年度问茶之旅。问茶,这是个讨巧的叙述,普通话就是找茶和买茶。 老六是嗜茶的。他在广州的茶圈和设计师圈里都小有名气,一泡茶喝上两口,茶叶的山头和采摘年份,甚至制作工艺,他都判断得八九不离十。虽然仅限于普洱和白茶,但这水平,已经让他征服了一大批茶友。“问茶”是老六设计师身份的产物,这样的“包装”显得有格调、高端。 所以每年的问茶之旅,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一是要找到好茶,二是要对得起茶友。早些年他也去过云南,但普洱市场已经资本化,靠工资过日子的他插不进手。 在茶界,流传着“世界茶看中国,中国茶看福建”的说法。关于福建哪里的茶最好,老六查了不少资料,最初以为在宁德福鼎地区、武夷山脉一段,后来在宋朝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和赵汝砺的《北苑别录》里,发现屏南才是史上的皇家茶园。 屏南广坑,问茶之路。 屏南古属福州,《新唐书》有说在北苑贡茶流行之前,这里的贡茶名叫“腊面”。茶之所以在中国兴盛,宗教和文化在背后的助力是不能忽视的,欧阳修在《归田录》里说到的“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指的就是龙凤团茶。当时的王公将相都知道,“黄金可得,龙凤难求”,龙凤团茶,产地就在屏南与建瓯的交界处。 对于茶本身的基本评判,老六把海拔和树龄放在并列第一。海拔高,证明茶的生长环境好,寒冷会让茶树少病虫害;树龄老,茶树的酚类物质就多,口感和耐泡程度非一般茶能比。 屏南平均海拔830米,天山山脉、武夷山脉和鹫峰山脉在这里交汇,历史上的御茶园又有据可考,这些标准让老六认定屏南有老茶树。 农户屋边的柴火,但这其实是老茶树。 但茶叶生长靠天指地,从不看人发芽,进入屏南境地的那张罚单,像一个隐喻,暗示着今年的问茶之行,将有些许磨难。 看着很鲜嫩,但一芽两叶的采摘,会给后期的排水带来阻碍。 “还记得去年清明节我们采茶吗?只有1℃,穿着四件衣服还冷得发抖。”老黄是从洛阳赶到屏南问茶的茶友,这几年他和老六都会在屏南相遇。去年看老六冷得直跺脚,老黄送了一双加厚的海魂袜给他,今年老六就是穿着这双袜子出发的。 到了屏南以后,老六发现今年的气温,短袖就能应付,厚袜子穿不住了,广播里还一直在说今年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少了四成。老黄说今年的茶估计没戏,要么没发芽,要么一抽芽就打开了。 3月28日,小古不得不带着老六和老黄到屏南最好的几个茶区——爱岭、广坑、双溪、郑山——去问茶。 爱岭村茶树,虽然有菌类包裹,但证明生态环境没有被过多破坏。 这些村子海拔大多在900米到1000米,常年云雾缭绕,有些村子已经荒废,但村子周围的田埂和后山上,还保留着大量被遗弃的茶树,茶树失去管理以后,会逐渐野化。中国就有一批茶客对野化后茶气的清冽趋之若鹜。 “果然没芽,今年完蛋了。”老六一边担心没法实现对朋友们的承诺,一边担心起屏南的未来了。 “福州弃儿” 在外人看来,小古的决定或许让人难以理解。 最初,他在上海通过计算机和世界各地的人做贸易,每个月可以挣一万多元。在2008年前后,这笔钱相当可观,但他受不了老板娘给他发工资时的一副臭脸,“单子是我接回来的,钱是我挣的,发个工资还扭扭捏捏,太没意思了”。 用计算机做生意在那个时候是朝阳产业,从2011年到2019年,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额从6万亿元发展到34.8万亿元。小古的放弃令人十分不解,尤其是在屏南,这样的情况十分罕见。 屏南千乘桥帮的小佛龛,供奉的是孙悟空。 高山层峦叠嶂,物质资源说不上匮乏,但也不富裕,屏南近几十年都是人口流出巨大,作为一个面积达到1500平方公里的区域,常住人口不过十几万人,相当于16个广州市天河区的面积却只住着1/10个天河区的人口。 因有销售经验,同乡包顺田请小古到他的茶厂帮忙。包顺田是屏南茶叶局前局长的儿子,也是小古的中学同学。 不得不承认小古的好学,在茶厂里,他研究起采茶、萎凋、晒青,甚至整个福建茶叶贸易史。当然,这与他从小就采茶有关,更何况他还读过农学院的茶叶专业。当这些因素堆积在一起,就构成了小古的人格特点:勤奋、诚恳、对家乡极度热爱。 小古家就在公路边上。 这些特质在老六看来,与“濒危”的古树茶一样可贵,“商品社会里,有钱可以买到大多数想要的东西,但好人和好茶一样,纯真的品质,千金难求”。 不过小古也有自己的困惑,他说好茶自古以来就是贵的,“小时候一碗扁肉(云吞)才几毛钱。但采一天茶有两三块钱;现在一碗扁肉五块钱,采茶就算100元工资日结也没人肯干。四五斤茶青才做出一斤茶,所以好茶一直就不是便宜的东西”。 屏南的扁肉,和沙县的不完全一样 当世界进入海洋争霸时代,屏南茶叶被制成绿茶和红茶,通过福州出口。当时因为茶叶好,屏南的茶卖得极贵。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说,中国依靠茶叶贸易获得了大量外汇,也就是白银。 当财富流入屏南,再次激发了屏南人种茶、采茶和制茶的热情。直到乾隆年间实行"一口通商"政策,福州口岸关闭,外贸交易必须南渡广州十三行,屏南茶叶面临第一次发展困境。 如果说屏南的好茶得益于高山层峦叠嶂,那没落大抵也因为交通不便。出口道路堵塞,国内市场又被其他茶叶品牌占领,这种困境悖论虽在清末被短暂打破(《南京条约》开放福州口岸),但在现代工业发展的浪潮中,又再次出现。 三个山脉交接,三条河流也在棠口汇合,才有了文人墨客的往事。 与其说是屏南的茶叶开始衰败,不如说是整个屏南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渐迷失。 当地政府对屏南发展最核心的担忧是人口少:“过去没有什么打工的概念,后来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前靠山吃山,现在都往城里跑,无论发展什么产业,都无法形成合力……而且我们总是觉得好像什么都有,但又什么都拿不出手。” 那些留在屏南的人,后来开始学习种菇。当时发展种菇事业,好多人都上山去砍杂木来做培育基,“我还写信给政府,说这样下去环境会被破坏掉”。小古说那时候他没有留意到,很多人因为种菇,每年也有几万元的收益。 种菇后来也成为了屏南流行的产业 不过这让他看到屏南甚至整个宁德都是这样,有什么可以赚钱的,大家就一窝蜂去做,没有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 屏南经济发展一直靠后,当地一度流传着“要将屏南划归福州,回到福州十邑的文化圈,但因为屏南太穷,福州不愿意”的传言。 曾经托起屏南江湖地位的茶叶,在这个时候看起来摇摇欲坠。 虽然海拔高,但历史上屏南仍属福州文化 小古恨极了这种发展方式,在老同学的茶厂干了两年后,他决定自己上山问茶,按传统方式采茶、制茶。他是爱茶的,这种爱,和老六、老黄的爱别无二致。 天价茶 和城市创业不同,小古在家乡创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被质疑。这是中国乡村的一个特点,对于曾经离开家的年轻人,家乡会给他们贴上标签——你长期不在,家乡的事你不懂,你对家乡没有过贡献。 屏南广坑,在石缝里长出的一株茶树。 但大城市的生活履历赋予了他观察家乡新的角度:我知道哪些东西是珍贵的。小古指的是那些被遗忘在屏南各个村落和山头的荒野茶树。 中国城市发展灯红酒绿,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寻找各自的城市梦,而那些世代都未离开过故土的中老年人逐渐老去,甚至魂归大山。 在茶盐古道上的屏南,这些年出现了大量空心村。按照风水来说,这些依山而建的村落,处在极好的地理位置上,极目远眺,山分五色,如今尽是残垣断壁,以及驼背的老人与长满青苔的青石板。 留在当地的人逐渐老去,但他们仍旧延续了传统的习俗。 从洛阳来屏南问茶的老黄,说起去年在屏南一个村口看到的一幕:一位老大爷,颤颤巍巍地拿着刀在砍一个大南瓜,可就是没劈开,瓜不劈开,他就没有吃的。 小古心里的道德天平有时会像个跷跷板,在困局中不停摇摆:正是因为茶树疏于管理,才有了如今的岩韵和枞韵,才有那种清高悠远的香气,规模种植的茶树完全不具备这些特点。 屏南爱岭村,很多房子已经破败 在他眼里,这些珍贵的茶树,却建立在残破和无人管理的基础上。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茶叶给屏南散播光明,又投下阴影,虽然只有那些有洞见的人才能看出这一点,却让小古十分矛盾。 内心的矛盾很快就被现实击垮了,2020年清明那会儿,正是疫情肆虐的时期,随着疫情逐渐受控,年轻人再次外出打工,一些茶园的采茶工人,也都涌向了城市。甚至有茶园因为找不到人采茶,用挖掘机挖掉了150亩古茶树,重新种了新的改良品种,利用机械化采摘,一斤茶青的成本只要几块钱。 屏南爱岭村后山,老人家种地,需要大量的化肥。 还是只能靠老人家。小古在各个有古树茶的村落,都找到了“代理人”。他会不断向代理人询问茶叶的长势和劳动力是否足够。顺利的话,代理人会安排好村里或者邻村的、还有劳动力的人采好茶,再通知小古来收,茶叶交易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在这种原始的状态下完成的。 基于茶叶的品质无忧,小古做的红茶在宁德地区的茶王赛里,也拿过金奖、银奖。小古对拿奖不以为意,他说这个奖是面向市场的,评委喜欢够香的茶,就拿香气高显的参赛,拿奖也不难。 茶青。采到茶青只是制茶的第一步。 我们总以为获奖的茶会被卖上天价,但在茶叶交易的前段环节,这些溢价并没有出现,小古说,对于茶人,拿奖只证明原料和工艺过得去,无关交易价格,有时候甚至为了支持朋友,拿奖的茶可能还得降价。 对于市场上经常出现的天价茶,一个形象的说法是,一个艺术家遇见了好的原料。对茶来说,好原料是岩茶,岩茶本身就有极大的资源稀缺性,而艺术家,就是那些非常有名的师傅。这两者结合起来,才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半夜12点多,茶人还是要不停地工作。 当然,岩茶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茶,从茶树生长到采摘、制作,每个环节都是极致美学,只有极高的文化底蕴才欣赏得来,所以岩茶本身就在茶叶的金字塔顶端。当然,天价也不排除另一个作用——洗钱,和艺术品拍卖市场一个道理。 由茶叶解读出美学和哲学意味,正是小古爱茶的另一个原因。所以对于屏南茶叶的现状,他有百般忧愁。 2020年因为屏南茶叶市场萎缩,屏南撤销了茶叶局,小古觉得自己的苦苦坚持似乎被一下子卸了力。 茶叶的萎凋车间,这个车间的核心竞争力是够干燥。 人们对撤销茶叶局的解读很多,主流的说法不外乎“周边的福鼎、福安才是现代的茶叶重镇”:福鼎有如今席卷市场的白茶,福安有众多茶叶研究所和茶叶交易基地,而拥有众多老茶树的屏南,成规模的茶叶加工厂只有十家左右。小古的同学、包顺田的厂,已经是屏南最大的茶厂,如今一年的加工量,还不到20万斤。 为了理想只做荒野茶的小古,一年产量不过几千斤,老六和老黄每年从他手里带走的茶,只是一小部分,这几千斤茶并未让小古翻身,他仍旧住在乡道旁的一栋老宅子里。有天早晨,老六想借用小古家的洗手间方便,老黄建议他去隔壁的公共厕所,说他家里的容易堵。 离开的,留下的 过去的宁德经济总量排全省最末,俗称“闽东老九”,全地区9个县有6个是贫困县,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 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恩说,屏南,在宁德地区的发展序列里,又是靠后的。 能源产业,当地的支持产业之一。 现在的宁德有了以能源为首的支柱产业,风能和水能发电成了GDP的榜首,上市公司宁德时代成了代表;他们还喜欢说另一个人——陆正耀,瑞幸咖啡的创始人,屏南如今为数不多的名人之一。为了支持家乡建设,陆正耀将瑞幸咖啡的烘焙厂设在了屏南。 当说完这些,屏南似乎就没有太多底气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了。以往的辉煌和文化也可以聊聊,但实际上也很难说出个子丑寅卯,不过当地人倒是会以屏南县城一个十字路口的武状元雕像为荣。 小古说,屏南史上有一条重要的“茶盐古道”,小户人家的茶叶和盐都是挑夫担着担子去交易的。当时为了防止路上有劫匪,很多挑夫有习武的习惯,因此当地具备了培养武状元的土壤。 屏南县城武状元的雕像。 来自洛阳的老黄补充了一个观点,充分体现了他对少林武功的热爱。他说是因为少林寺被排挤,少林武僧躲难至屏南,才有了挑夫习武的习惯,而且挑夫参习的就是少林武功。 这一切在短期内很难考证,但沉浸在过往的辉煌不过是为了掩盖眼下的失意,这就像屏南当下的叙事脚本,对过往有无限的遐想,但面对未来,总是有所顾忌。 屏南人对家乡基本达成一个共识——没有自己的主打产业,所以不够自信;因为不自信,所以在选择主打产业的时候总是跟风。这也正是小古回乡创业陷入困境的原因。 屏南有规模的茶厂,不过十家左右。 3月末,屏南县县长到包顺田的茶厂视察,包顺田向县长报告说:“茶叶这个东西,都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我们做企业的,要摸索出屏南究竟应该做什么样的茶,政府也应该扶持一两家龙头企业,然后拿出一两款好茶向外推广。” 这种发展思路其实和福鼎类似,2010年上海茶博会上,福鼎市政府第一次推出福鼎白茶,如今,白茶和太姥山成了福鼎的名片。 包顺田那番话隐含着另一个意思:希望政府在产业前端也给予支持。周边县市在推进茶产业的时候,第一年给茶农每年每亩补贴500元,第二年300元,第三年200元,因为种茶的前几年,几乎是零收益,但政府的这个行为,很快就能让产业具备做大的基础。 仔细看看这个碑,原来有瑞幸CEO的名字,现代与过去原来一点都不遥远对吧。 新周刊记者还采访了一位前国土局官员及一位政协委员,他们有相似的担忧:茶叶这个市场好像也不大,红茶又过时了,岩茶工艺太严格,我们好像又不会,发展白茶又名不正言不顺。 包顺田觉得自己和政府并没有在同一个维度上聊这个问题:“政府不要太管市场的事,应该看屏南合适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对于中国市场来说,没有哪个茶不行,只有哪个茶不流行。只要茶足够优秀、足够有故事和文化,屏南的这点茶拿到全国市场,一下就没了。” 制茶是一个繁琐而考究的过程。 其实,包顺田知道屏南的茶是如何输给福鼎的,因为福鼎沿海,海拔较低,所以发芽早,产茶快,卖得也快。等到高海拔屏南的茶上市,市场已经被福鼎瓜分完毕了。 福鼎对茶叶的品控也十分严格。品控,大概就是安溪铁观音倒下后的墓志铭。 屏南撤销了茶叶局后,卸任的茶叶局局长联系了小古,说他们打算在清明节后结伴到周边的茶叶重镇去看看,和兄弟政府聊一聊,看能不能将一些不错的茶厂引到屏南来,发挥一下带头作用。 屏南也在发展网红小镇,这是夏地的一个咖啡馆。 2020年年末,屏南挂牌了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潘家恩是执行院长,也是重庆大学的博导,土生土长的宁德人。“屏南遇到的问题,和全国许多县域经济体类似,空心化、陷入县域经济的区域竞争中。” 对于被挖掉的150亩古树茶,潘家恩和小古同样痛心:在把县域品牌做起来之前,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宝贵财产,不可复制的财产。 即便是夜里,茶人也要对有损坏的制茶器进行修补。 潘家恩觉得,屏南的优势实际上就是高海拔。高海拔意味着环境和生态好,在促进内循环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海拔就是稀缺资源,而茶树是高海拔的生态标志之一,加上历史上的茶盐古道、贡茶产区,这一切都是屏南最珍贵的历史财富。现在,研究院正在和屏南政府合力恢复茶盐古道的生态。 对于这个决定,小古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但他还是决定扎根到做茶的事业中:“如果屏南的茶产业在我这一代人手里无法振兴,未来永远都不会有机会了。”小古说完,干掉了杯子里的黄酒,摇摇晃晃地走进茶厂去给老贡眉焙火。 完美的平衡,可见当地人还有烧柴的习俗。 那已是夜里12点多,一旁的老六和老黄已经意兴阑珊。过几天,他们将带着小古的茶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小古将仍旧守在自己的茶厂边。 小古的茶厂旁有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别墅只要3999元/平方米,还没有公摊。小古每次经过的时候都会自嘲一下:“在屏南,谁会买哦!” 山里月朗星稀,没有一丝云彩,今年的早春,真是格外干旱。 月朗星稀,走的走,留的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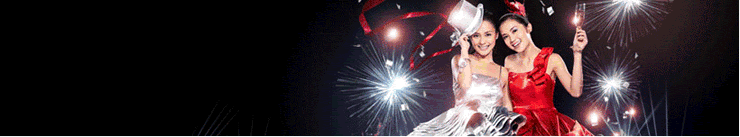
 |Archiver|mobile|The little black house|Shanghai WTO Net
( 沪ICP备10034107号-3 )
|Archiver|mobile|The little black house|Shanghai WTO Net
( 沪ICP备10034107号-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