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жҙ—жҫЎд№ғдәәз”ҹе°ҸдәӢпјҢеҮЎе°ҸдәӢиҖҢдёҚеҸҜйЎ»иҮҫзҰ»иҖ…пјҢеӨҡйҡҗе–»еӨ§гҖӮеҹәзқЈж•ҷжҳҜеҸ—жҙ—пјҢеӨ§иҙқеЈіжІҫзӮ№ж°ҙж„ҸжҖқж„ҸжҖқпјҢи·ҹдёҚжІҫж°ҙзҡ„ж—ҘеҗҺе°ұиө°дәҶдёӨжқЎйҒ“гҖӮдҪӣж•ҷжІЎеҗ¬иҜҙиҝҮпјҢдҪҶйҮҠиҝҰзүҹе°јдҪӣеҗғе®ҢйҘӯжҳҜжҙ—и„ҡзҡ„пјҢжҙ—е®Ңи„ҡжүҚж•·еә§иҖҢеқҗпјҢз»ҷйЎ»иҸ©жҸҗдёҠйӮЈдәӣдә‘дҪ•дә‘дҪ•зҡ„иҜҫгҖӮ
з«Ҝи„ёзӣҶжҙ—жҫЎжҳҜжҲ‘们еӯҰж Ўзҡ„ең°ж–№зү№иүІпјҢеӯҰж ЎејҖиҫҹзҡ„жҳҜдёҖдёӘеҺҹе§Ӣжөҙе®ӨпјҢйҷӨдәҶж°ҙпјҢе…¶д»–дёҖеҫӢжІЎжңүгҖӮз”ҡиҮіиҝһж°ҙйғҪеҶ·зғӯдёҚеқҮпјҢеёёеҗ¬и§Ғж»Ўе®Өжө“йӣҫдёӯдёҖйҳөе°–еҸ«пјҢеҶҚдёҖзңӢж°ҙдёӢе°ұжІЎдәәдәҶпјҢеӨ§е®¶йғҪиҗҪжұӨйёЎдёҖиҲ¬з«ҷеңЁж—Ғиҫ№пјҢеҪ“ж—¶йӮЈж°ҙзғ«еҫ—иӮҜе®ҡжү“дёӘйёЎиӣӢиҝӣеҺ»йғҪжҲҗиҠұгҖӮжүҖд»ҘеңЁжҲ‘们еӯҰж ЎиҜ»иҝҮд№Ұзҡ„дәәпјҢйғҪи®°зқҖдёӨ件дәӢпјҢдёҖ件жҳҜеҗғйҘӯпјҢеҶҚдёҖ件е°ұжҳҜжҙ—жҫЎгҖӮеүҚиҫ№йӮЈд»¶жІЎжІ№ж°ҙпјҢеӨ§е®¶еҗғе®ҢдәҶиҝҳеҫ—еҺ»зҹҘиҜҶжө·жҙӢйҮҢжүҫиҙҙиЎҘпјҢйӮЈдјҡе„ҝзҡ„еӯҰз”ҹдёӘдёӘеҮәиүІпјҢдј°и®Ўи·ҹеҮ¶зҲ№йқўеүҚжңүеӯқеӯҗзҡ„еҺҹзҗҶе·®дёҚеӨҡпјҢйҘҝеҮәжқҘзҡ„зІҫзҘһеӨҙеҲ«иҜҙдҪ“дјҡиӢҸдёңеқЎгҖҒйҷ¶жёҠжҳҺпјҢеҶҚеҺүе®ізӮ№зҡ„иҖҒеӯҗдёҖйҒҚе°ұйҖҡеҲ°дәҶеҫ—ж„ҸеҝҳиЁҖпјҢеҶҚдёҖйҒҚжңүиҜқйғҪеҢ–жҲҗдәҶжө…笑пјҢж №жң¬дёҚз”ЁеңЁзҺ°е®һдёӯи·Ңи·ҹеӨҙеҸ—зҡ®иӮүд№ӢиӢҰгҖӮ
еҸҰдёҖдёӘе°ұжҳҜжҙ—жҫЎпјҢвҖңжІ§жөӘд№Ӣж°ҙжё…е…®еҸҜд»ҘжҝҜеҗҫзјЁпјҢжІ§жөӘд№Ӣж°ҙжөҠе…®еҸҜд»ҘжҝҜеҗҫи¶івҖқпјҢеҪ“еҲқеұҲеҺҹе®һеңЁжҪҮжҙ’пјҢд»Җд№Ҳж°ҙжҙ—д»Җд№ҲйғҪжңү讲究гҖӮжҲ‘йӮЈдјҡиҝ·жқЁз»ӣпјҢзӣ–еӣ еҘ№еҶҷдәҶйғЁгҖҠжҙ—жҫЎгҖӢпјҢжІЎи®°й”ҷзҡ„иҜқпјҢеұҲеҺҹиҝҷиҜқе°ұеҚ°еңЁдёҠйқўгҖӮжқЁз»ӣжҠҠжҙ—и„‘еӯҗе®ҡд№үдёәжҙ—жҫЎпјҢиҖҒеӨӘеӨӘеҺүе®іпјҢдёҖеҲҮиӢҰйҡҫйғҪиў«еҘ№й•Үе®ҡжҺүдәҶгҖӮиҮідәҺдёәд»Җд№Ҳз»ҷиҝҷд№ҰеҸ–иҝҷеҗҚпјҢдёҖзӣҙжғідёҚйҖҡпјҢеҸҲжІЎйҘҝзқҖиӮҡеӯҗеңЁжҲ‘们еӯҰж Ўжҙ—иҝҮжҫЎпјҢжқЁе…Ҳз”ҹз«ҹеҰӮжӯӨи§Јеҫ—дёӘдёӯж»Ӣе‘ігҖӮ
жҙ—жҫЎзҰ»дёҚејҖйҰҷзҡӮпјҢйӮЈж—¶жҳҜең°ж–№дҝқжҠӨдё»д№үпјҢеҗ„ең°зҡ„дёңиҘҝйғҪдёҚи¶Ҡз•ҢпјҢдјји®°зқҖдёҖз§Қиқ¶йҰҷзүҢйҰҷзҡӮпјҢжө…з»ҝиүІпјҢжҜҚдәІд№°еӣһ家жҲ‘е…ҲжӢҶеҢ…пјҢж”ҫеңЁйј»еӯҗдёҠдёҖйҳөзӢӮе—…пјҢйҰҷзҡӮзҡ„еҢ…иЈ…зәёдёҖзӣҙеёҰеңЁиә«дёҠпјҢж”ҫеҲ°жІЎе‘ідәҶжүҚиӮҜдёўжҺүгҖӮдҪҶжҲ‘жңҖе–ңж¬ўзҡ„иҝҳжҳҜеҚҺе…үзүҢжҙ—иЎЈзҡӮпјҢеӨ§еӨ§зҡ„дёҖеқ—пјҢдёҖжҺ°дёӨеҚҠпјҢйӮЈе‘ійҒ“ж·ұе…ҘдәәеҝғпјҢжІЎдәӢе°ұж”ҫйј»еӯҗдёҠй—»гҖӮжҲ‘еҜ№йҰҷзҡӮзҡ„жңҖеӨ§ж„ҹжғ…жҳҜеҸҜд»ҘжіЎиҪҜдәҶиЈ…иҝӣ瓶еҗ№жіЎжіЎзҺ©е„ҝпјҢзҲ¶жҜҚеұЎзҰҒдёҚжӯўпјҢзҹҘйҒ“иҝҷеӯ©еӯҗжҳҜеӨӘжІЎеҫ—зҺ©дәҶпјҢеҗҺжқҘе№Іи„Ҷж”ҫејҖжҗһжҙ»пјҢиҝһжҜҚдәІд№ҹи·ҹзқҖдёҖиө·зҺ©е„ҝдәҶгҖӮ
зҺ°еңЁжҜ”иҫғ讲究зҡ„жҙ—жі•жҳҜз”ЁжөҙзӣҗпјҢж°ҙдёҠж’’зҺ«з‘°иҠұз“ЈпјҢж—Ғиҫ№иҝҳжңүжқҜеҠЈиҙЁй…’пјҢйӮЈжҳҜиў«иө„жң¬дё»д№үи…җиҡҖеҫ—е°ҶйҖҸжңӘйҖҸж—¶ж‘ҶеҮәзҡ„е§ҝеҠҝгҖӮзңҹжӯЈзҡ„иұӘй—ЁеӨ§жҲ·йғҪе…ізқҖй—Ёжҙ—жңЁзӣҶпјҢз”ЁдёҠеҘҪжңЁжқҗеҒҡжҲҗжҫЎзӣҶжҲ–жҫЎжЎ¶пјҢйҮҢйқўжөҮж»ҡзғ«зғӯж°ҙпјҢиҮӘ然еҸҳжё©еҗҺиҝӣеҺ»жіЎдёӘжҠҠе°Ҹж—¶пјҢеҶҚеҮәжқҘдёҖиә«е…ғж°”пјҢеҶҷеӯ—з”»з”»йғҪдёҖ马平е·қпјҢз•…йҖҡж— йҳ»гҖӮ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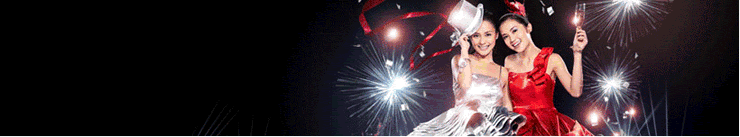
 |Archiver|mobile|The little black house|Shanghai WTO Net
( жІӘICPеӨҮ10034107еҸ·-3 )
|Archiver|mobile|The little black house|Shanghai WTO Net
( жІӘICPеӨҮ10034107еҸ·-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