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08年有两个重要的事件,让我们的注意力从中心城市转向偏远的农村地区。一是从年初开始世界性粮食危机重新回头,二是“5·12汶川大地震”,这两个事件让我们关注到,在中国广大内陆还有人口稠密的人类聚居地。
请注意这里用的是“人类聚居地”,而不是简单地用“城市”或“农村”。自有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就是在各种大小不一的聚居地生活着的。
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于城市与乡村的划分,并不像我们这几十年来,是以城市户口及建设用地的国有与集体性质来区分的。如美国统计局对“城市地区”的定义是,凡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386人的区域,即可称为“城市地区”;另一个概念是“城市周边地区”,主要是指位于城市地区周边,同时每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93人的区域;在城市地区、城市周边地区之外,就是乡村地区。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城镇与农村的区别也只是聚居密度与规模的区别,并未有城镇土地性质与农村土地性质的区分,更无居民户口身份的区别。因此,用“人类聚居地”这个词,更能平等地反映人们生存居住的状态。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存在于过去数十年中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也许只是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极短时间内、极个别区域的特殊制度产物,当然也绝非成熟的制度。然而,正是这种不成熟的制度产物成为走向全面城市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背景。
大城市核心地区的房价在短短3年内增长了近两倍,暴涨的房价与无力购房人的不满使得3年来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从未停止过。这种普涨形势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严控土地供应与地价上涨之间的必然联系。人们将怒火投向房地产开发商,认为是他们推高房价、牟取暴利,即使是最有责任心的地产商在民众心中也成为反面角色。
中国人多地少,大城市往往也选址于农业发达、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城市发展占地与农地矛盾十分激烈。尽管在全国范围内五分之四的人居住在所谓的农村地区,但我们的城市规划对此类地区几乎是视而不见,因为所谓城市规划就是规划国有用地,农村地区是属于村镇规划范畴的。城市规划总图上,也一律是用色块将各种城市建设用地标识出来,而农村居民点则大多是底图上的背景色彩而已。习惯于遵从上位规划的各级规划编制者,也往往将旧村改造作为提升城市形象的主要面子工程,将旧村落作为待改造用地,重新大拆大建。
对于传统聚居地的漠视引起了必然的反弹,结果就是原住民面对拆迁时的私搭乱建、漫天要价。大量的社会资源与财富在一建与一拆中被损耗,大量的人力资源浪费在无效的内耗之中。
事实上在拆迁还建、货币补偿、重新规划、土地整理等一系过程中,所有成本最终都由后来者埋单,前期社会资源投入的高浪费直接造成了高地价,房地产土地供应市场陷入怪圈。
而这一切,仅仅是人为割裂人类聚居地这个城市化巨大背景下的副产品。
现代城市发展源于规划,但不切实际的规划却对城镇原有形态产生了可怕的影响。例如,北京近郊任何一个完整的村落,都具有数百年的历史和生态轨迹,如今随着城市的膨胀,已不得不被淹没在城市蔓延带中了。我们的城市规划往往是大笔一挥,霸道地将其视为拆迁改造的对象。一夜之间,规划者笔下的一条线就可能造成一个数百年村落的消失。
我们正走进一个误区,只有经过规划的、土地征用过的,变成国有用地并进行出让的建设用地区域,才是合格用地。而广大的乡村地区,特别是数百年来自发形成的人类聚居地,是不合规划的,必然拆除改造的。这是造成新的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
重新给予数以亿计的人口居住聚落以合法存在的身份,而不是在各种城市规划中将其置于被拆除的命运,这是对数百年人类聚居历史的尊重,更是实现无差别的人类聚居梦想的起点。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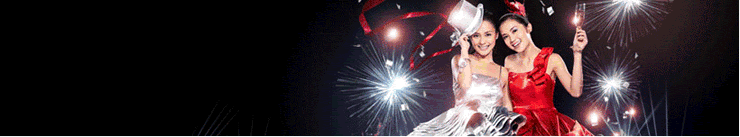
 |Archiver|mobile|The little black house|Shanghai WTO Net
( 沪ICP备10034107号-3 )
|Archiver|mobile|The little black house|Shanghai WTO Net
( 沪ICP备10034107号-3 )